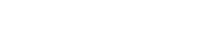雨比她想象的大。
她穿着白色的棉布裙子出门时,天还只是阴着。
走到半路雨就泼下来了,她撑开伞,可没什么用,风把雨丝吹得斜斜的,裙子很快湿透,沉甸甸地裹在小腿上。
这条裙子是前年阿婆扯布做的,领口开得小小的,袖子到肘弯,是她在家里穿惯的衣裳。出门时懒得换,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山路被雨水泡得松软,每一步都陷进去,再费力拔出来。那双布鞋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,鞋里灌了水,走一步,咕叽一声。
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。
她忽然站住了。
低头看着自己手里——一把伞,就一把。
她是来送伞的。可她只带了一把伞。
那她来送什么?送完自己淋回去?
她站在雨里,愣了好几秒。
山路拐过一个弯,还是没有他的影子。她站住,喘了口气,雨水顺着伞骨滑下来,在眼前挂成一道帘子。
要不……回去吧。
这个念头刚冒出来,脚却还在往前走。
转过又一个弯,她终于看见了他。
他站在一棵老樟树下,背对着她,画夹抱在怀里,用外套裹着。雨水顺着他低垂的头发往下淌,从后颈滑进衣领,把肩背那块洇成深色。
她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,忽然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“陈……陈先生。”
声音被雨冲得很轻。
他回过头。
看见她的那一瞬间,他脸上闪过一丝什么——很快,快得像是她的错觉。然后那表情敛去了,只剩下惯常的平淡。
“你怎么来了。”
她举了举手里的伞:“阿婆……阿婆让我来的。”
他看着她,没说话。
那目光太长了,长得她垂下眼,盯着自己沾满泥巴的鞋尖。
“伞给你。”她把伞往前递,“我先回去了。”
他走过来。
停在她面前,低头看她。雨水从他发梢滴下来,落在她伸出去的伞面上。
“你淋成这样,让我打伞?”
他的声音低低的,哑哑的。
她没抬头,只是把伞又往前递了递:“我没事。”
他没接。
反而伸手,把她举伞的手轻轻按了下去。
“一起走。”
他说完,从她身边擦过,往前走。
她愣了一下,转身跟上。手里还举着那把伞,举也不是,收也不是。最后她收了伞,抱在怀里,和他并肩走在雨里。
雨打在脸上,凉凉的。
谁都没说话。
山路很长。她低着头,看着脚下的泥泞。余光里能看见他的袖子,湿透了,贴在小臂上。
她想起那天晚上,这只手攥过她的手腕,这只手碰过她的脸。
她垂下眼,往旁边挪了挪,离他远一点。
他没动。
可没走几步,她又不知不觉挨近了。
山路窄,只能这样。
她对自己说。
雨越下越大。她那件白色棉布裙子已经彻底湿透,贴在身上,冷得她有点发抖。可她咬着牙,一声不吭。
“冷吗?”
他忽然问。
她愣了一下,摇摇头:“不冷。”
话刚说完,一阵风刮过来,她没忍住,打了个哆嗦。
他没说话,只是把外套从画夹上拿下来,递给她。
“穿上。”
她看着那件外套——已经湿了半边,可总比没有好。
“不用,你……”
“穿上。”
他打断她,语气很平,没什么情绪。
她接过来,披在身上。
外套上有他的气息,被雨水冲得很淡,可还是有一点。那气息钻进鼻子里,她鼻子忽然就酸了。
她低下头,假装在整理袖口。
他怎么那么……
冷淡。
可这不是她要的么。
眼眶热热的,她拼命忍着。
别哭。
别哭。
有什么好哭的。
她深吸一口气,把那股酸意压下去。
---
回到老宅时,天已经快黑了。
阿婆站在廊下张望,看见他们俩淋成那样,哎哟一声就跑过来。
“这是怎么弄的!囡囡你浑身都湿透了!快去换衣裳!”
她被阿婆拉着往里走,经过他身边时,听见他在后面说:“阿婆,是我不好,让沉小姐来接我。”
她脚步顿了顿,没回头。
上楼换了干衣裳,把那件湿透的棉布裙子丢进脏衣篓里。沾了泥,怕是洗不干净了。
她站在镜子前,看着里面那个人——脸色苍白,眼睛却红红的,鼻尖也红红的,狼狈得很。
她想起刚才在山里,他站在她面前,把外套递给她时的那个眼神。
不是心疼。
不是关切。
是一种她看不懂的、复杂的、像是压着什么东西的眼神。
她看不懂,也不想看懂。
晚饭他没下来吃。
吴妈说他有点咳嗽,喝了姜汤就睡了。
她坐在餐桌前,面前摆着饭,一口也没动。
阿婆看她一眼,没问什么,只是把那碗汤往她面前推了推。
她端起碗,喝了一口。
姜汤很辣,辣得眼眶又热了。
那天夜里,她躺在床上,睁着眼,看着天花板。
隔壁很安静。
她翻了个身,把脸埋进枕头里。
脑子里反复想的,不是那晚的事,不是他碰她眼角的那一下,甚至不是他把外套递给她时那个复杂的眼神——
她想的是自己。
想自己今天为什么要去。
为什么一看到下雨了就想到他,就拿伞出了门。
想自己走在那条山路上,又冷又累,鞋里灌满了水,裙子上沾了泥,狼狈得要命,却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想自己看见他站在那棵树下时,心里那一下——不是松了口气,不是放心了,是一种更深的、说不清的东西。
想自己和他并肩走在雨里,明明可以离远一点,却不知不觉又挨近了。
想自己披着他的外套时,闻到那一点点气息,听着他的语气,鼻子怎么就酸了。
她想了很久。
然后她想起一个词。
活该。
活该你这么难受。
活该你睡不着。
活该你心里堵得慌。
是你自己要去的。
是你自己走那条路的。
是你自己,明明知道不应该,却还是——
她翻了个身,盯着天花板。
眼眶又热了。
这一次,她没忍住。
眼泪从眼角滑下来,流进枕头里,湿了一小片。
她没出声,就那么躺着,让眼泪一直流。
反正没人看见。
反正……
她想,反正他也看不见。
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很静。
她哭了一会儿,慢慢停了。眼睛肿了,鼻子也堵了,难受得很。
可她心里那股堵着的东西,好像松了一点点。
只是一点点。
然后她想起一件事——他的外套,她忘了还。
还挂在楼下的衣架上,湿的,大概吴妈已经收走了。
她闭上眼,不想了。
可脑子里还是冒出一句话:
明天见到他,该说什么?
她不知道。
她穿着白色的棉布裙子出门时,天还只是阴着。
走到半路雨就泼下来了,她撑开伞,可没什么用,风把雨丝吹得斜斜的,裙子很快湿透,沉甸甸地裹在小腿上。
这条裙子是前年阿婆扯布做的,领口开得小小的,袖子到肘弯,是她在家里穿惯的衣裳。出门时懒得换,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山路被雨水泡得松软,每一步都陷进去,再费力拔出来。那双布鞋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,鞋里灌了水,走一步,咕叽一声。
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。
她忽然站住了。
低头看着自己手里——一把伞,就一把。
她是来送伞的。可她只带了一把伞。
那她来送什么?送完自己淋回去?
她站在雨里,愣了好几秒。
山路拐过一个弯,还是没有他的影子。她站住,喘了口气,雨水顺着伞骨滑下来,在眼前挂成一道帘子。
要不……回去吧。
这个念头刚冒出来,脚却还在往前走。
转过又一个弯,她终于看见了他。
他站在一棵老樟树下,背对着她,画夹抱在怀里,用外套裹着。雨水顺着他低垂的头发往下淌,从后颈滑进衣领,把肩背那块洇成深色。
她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,忽然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“陈……陈先生。”
声音被雨冲得很轻。
他回过头。
看见她的那一瞬间,他脸上闪过一丝什么——很快,快得像是她的错觉。然后那表情敛去了,只剩下惯常的平淡。
“你怎么来了。”
她举了举手里的伞:“阿婆……阿婆让我来的。”
他看着她,没说话。
那目光太长了,长得她垂下眼,盯着自己沾满泥巴的鞋尖。
“伞给你。”她把伞往前递,“我先回去了。”
他走过来。
停在她面前,低头看她。雨水从他发梢滴下来,落在她伸出去的伞面上。
“你淋成这样,让我打伞?”
他的声音低低的,哑哑的。
她没抬头,只是把伞又往前递了递:“我没事。”
他没接。
反而伸手,把她举伞的手轻轻按了下去。
“一起走。”
他说完,从她身边擦过,往前走。
她愣了一下,转身跟上。手里还举着那把伞,举也不是,收也不是。最后她收了伞,抱在怀里,和他并肩走在雨里。
雨打在脸上,凉凉的。
谁都没说话。
山路很长。她低着头,看着脚下的泥泞。余光里能看见他的袖子,湿透了,贴在小臂上。
她想起那天晚上,这只手攥过她的手腕,这只手碰过她的脸。
她垂下眼,往旁边挪了挪,离他远一点。
他没动。
可没走几步,她又不知不觉挨近了。
山路窄,只能这样。
她对自己说。
雨越下越大。她那件白色棉布裙子已经彻底湿透,贴在身上,冷得她有点发抖。可她咬着牙,一声不吭。
“冷吗?”
他忽然问。
她愣了一下,摇摇头:“不冷。”
话刚说完,一阵风刮过来,她没忍住,打了个哆嗦。
他没说话,只是把外套从画夹上拿下来,递给她。
“穿上。”
她看着那件外套——已经湿了半边,可总比没有好。
“不用,你……”
“穿上。”
他打断她,语气很平,没什么情绪。
她接过来,披在身上。
外套上有他的气息,被雨水冲得很淡,可还是有一点。那气息钻进鼻子里,她鼻子忽然就酸了。
她低下头,假装在整理袖口。
他怎么那么……
冷淡。
可这不是她要的么。
眼眶热热的,她拼命忍着。
别哭。
别哭。
有什么好哭的。
她深吸一口气,把那股酸意压下去。
---
回到老宅时,天已经快黑了。
阿婆站在廊下张望,看见他们俩淋成那样,哎哟一声就跑过来。
“这是怎么弄的!囡囡你浑身都湿透了!快去换衣裳!”
她被阿婆拉着往里走,经过他身边时,听见他在后面说:“阿婆,是我不好,让沉小姐来接我。”
她脚步顿了顿,没回头。
上楼换了干衣裳,把那件湿透的棉布裙子丢进脏衣篓里。沾了泥,怕是洗不干净了。
她站在镜子前,看着里面那个人——脸色苍白,眼睛却红红的,鼻尖也红红的,狼狈得很。
她想起刚才在山里,他站在她面前,把外套递给她时的那个眼神。
不是心疼。
不是关切。
是一种她看不懂的、复杂的、像是压着什么东西的眼神。
她看不懂,也不想看懂。
晚饭他没下来吃。
吴妈说他有点咳嗽,喝了姜汤就睡了。
她坐在餐桌前,面前摆着饭,一口也没动。
阿婆看她一眼,没问什么,只是把那碗汤往她面前推了推。
她端起碗,喝了一口。
姜汤很辣,辣得眼眶又热了。
那天夜里,她躺在床上,睁着眼,看着天花板。
隔壁很安静。
她翻了个身,把脸埋进枕头里。
脑子里反复想的,不是那晚的事,不是他碰她眼角的那一下,甚至不是他把外套递给她时那个复杂的眼神——
她想的是自己。
想自己今天为什么要去。
为什么一看到下雨了就想到他,就拿伞出了门。
想自己走在那条山路上,又冷又累,鞋里灌满了水,裙子上沾了泥,狼狈得要命,却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想自己看见他站在那棵树下时,心里那一下——不是松了口气,不是放心了,是一种更深的、说不清的东西。
想自己和他并肩走在雨里,明明可以离远一点,却不知不觉又挨近了。
想自己披着他的外套时,闻到那一点点气息,听着他的语气,鼻子怎么就酸了。
她想了很久。
然后她想起一个词。
活该。
活该你这么难受。
活该你睡不着。
活该你心里堵得慌。
是你自己要去的。
是你自己走那条路的。
是你自己,明明知道不应该,却还是——
她翻了个身,盯着天花板。
眼眶又热了。
这一次,她没忍住。
眼泪从眼角滑下来,流进枕头里,湿了一小片。
她没出声,就那么躺着,让眼泪一直流。
反正没人看见。
反正……
她想,反正他也看不见。
眼泪流得更凶了。
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很静。
她哭了一会儿,慢慢停了。眼睛肿了,鼻子也堵了,难受得很。
可她心里那股堵着的东西,好像松了一点点。
只是一点点。
然后她想起一件事——他的外套,她忘了还。
还挂在楼下的衣架上,湿的,大概吴妈已经收走了。
她闭上眼,不想了。
可脑子里还是冒出一句话:
明天见到他,该说什么?
她不知道。